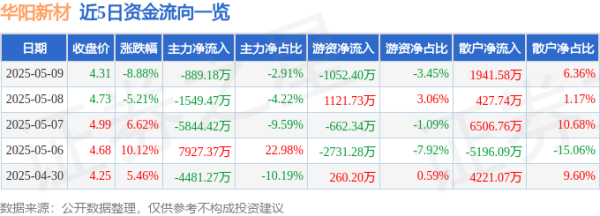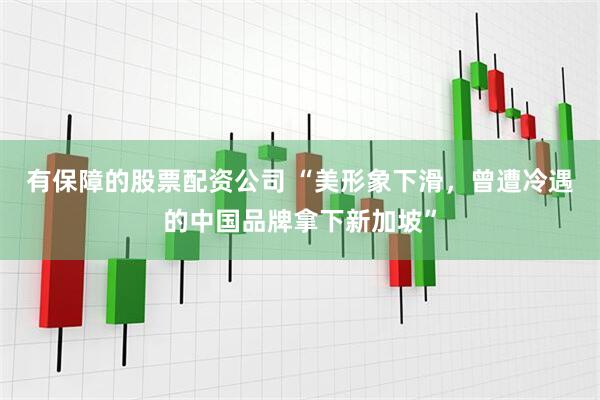近年来配资网首页官网,医药外企在中国市场的撤退愈发猛烈。
从进口药逐步退出国内公立医院体系,到辉瑞、罗氏等巨头先后关闭中国研发中心或裁撤在华研发业务,再到日本住友等药企纷纷抛售中国分公司。
在这背后是中国医疗政策、市场竞争与跨国药企战略转型之间形成的错综结果。
01
野蛮生长
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通过税收优惠、土地支持等政策吸引大量外资。1980年,首个合资药企中国大冢制药在天津成立,随后BMS、杨森制药等巨头纷纷在华建厂。
彼时,中国本土药企还是以仿制药为主,创新能力薄弱。而这些入华的医药外企凭借专利药物,迅速占据中国高端医疗市场,尤其在肿瘤药、心血管药等领域形成技术垄断。
并且,这些外企通过高薪招聘医药代表,迅速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。
比如辉瑞、拜耳等公司的一线代表薪资一般是本土企业的2-3倍,他们通过学术会议、回扣等方式将公司产品快速与中国医院绑定。2014年数据显示,外资药企在中国三甲医院的处方药占比超过60%。
此外,在2015年之前,外资药企还可以凭借“原研药”身份享受单独定价特权,与国产仿制药价格差异可高达数倍甚至数十倍。
比如辉瑞的降脂药立普妥专利哪怕2011年到期后,在中国市场仍可以以“原研药”身份维持高价(约7.6元/片),而国产仿制药仅0.2-0.3元/片。这一特权直至2015年才逐步取消,此前一直是医药外企的利润核心。
但在2015年之后,中国医药政策转向集采、医保控费和本土创新扶持,外资药企的高溢价模式的野蛮生长难以为继。其实,这一趋势,早见端倪。
2014年,外资药企在华销售增速已从20%以上骤降至5%-10%,裁员和业务收缩也就成为普遍选择。比如BMS就在当年12月宣布中国区裁员近千人的决定。
02
集体撤退
可以发现:近年来,医药外企选择“集体撤退”,是因为遭受政策、成本与市场的三重挤压。
一方面,药品集采等政策对外资原研药形成价格绞杀。中国自2018年推行的药品集采政策,通过“以量换价”大幅压低药价。这种模式固然惠及了万千患者,却直接压缩了外资药企的利润空间。
跨国药企的每一款原研药平均研发成本超20亿美元,为了回收成本不可能定价过低,自然难以与国产仿制药的低价竞争,只能被迫放弃国内集采或医保谈判。比如2024年第七批集采,医药外企原研药中标率已从35%暴跌至6%。
并且,在国内DRG付费模式下,医院为控制成本更倾向选择性价比高的国产仿制药。以肿瘤治疗为例,进口抗癌药单日费用常超千元,而国产仿制药价格仅为零头。这种政策导向加速了进口药在公立医院体系的退场,2025年多地三甲医院进口药占比已不足20%。
另一方面,外资还面临着国产替代强势崛起的挑战。
近年来,中国本土药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提升质量,在抗生素、降压药等领域已实现90%以上的国产替代率。恒瑞、百济等企业更在创新药研发上突破技术壁垒,有望冲击MNC部分产品的地位。而在本土竞争加剧下,日本协和麒麟在华收入骤降至总营收的3%,市场被严重挤压,最终2024年它以7.2亿元出售中国业务,转为代理商模式。
此外,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,但由于定价自由度问题,跨国药企正面临“规模大、利润低”的困境。比如阿斯利康PD-L1抑制剂“英飞凡”在中国的年治疗费用仅4.3万美元,不足美国的1/3。
叠加国内反腐监管趋严,数据管制加强,人力与运营成本上升,医药外企在华研发投入意愿近年来显著下降。2024年,中国本土获批的50余款I类新药中,跨国药企占比还不足10%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,跨国药企并非全面退出中国,而是调整其中国策略。
一是聚焦高端市场,比如罗氏等跨国药企保留肿瘤、罕见病等高壁垒领域,通过特药渠道维持高利润。
二是转向临床试验外包或License-in模式,比如跨国药企更倾向于将早期研发外包给中国本土CXO企业(如药明康德、康龙化成),而非自建完整研发链条。2023年,中国CXO企业营收增速普遍超过30%,而跨国药企在华研发中心数量增长几乎停滞,部分企业(如葛兰素史克)甚至缩减实验室规模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2025年国家医保局已提出“新药早期准入”等政策,试图在控费与创新激励间寻找平衡点,或许将来能为外资及本土药企的原研药腾出更多利润空间。
(转自:药闻社)配资网首页官网
要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